「有太多的驚奇,就在你隔壁,台北廣播電台」。這段由蔡依林、殷正洋義務錄製的jingle,十餘年來不時迴旋在腦海,只為提醒自己「永遠不能遺忘那群在電台最潦倒時期,曾經伸出援手的節目義工。」 1996年8月1日凌晨台北市議會在李姓女議員主導下,以「黨政軍應退出媒體」為由,如數刪除台北電台八千餘萬元的人事及業務預算。台北電台瞬間由盛轉衰幾近歸零,百餘位員工面臨移撥或失業命運。我雖未經歷團隊崩離的感傷和不知誰掌管明天的茫然;但兩年後我卻接掌了百廢待舉、形同廢墟的「萬貫家業」。 在沒人、沒錢的窘境下,電台為保留執照,依舊維持十八小時播音(貼切說法是墊音樂)。不忍讓曾經叱吒風光的電台在我手中斷氣,不願扮演末代台長的我,開始捲起袖子向外求援。在師長、同學、朋友的穿針引線下,與我素昧平生的廣播界、藝文界、影視界、電台老同事及素人義工近三十人,竟然如即時雨般地適時伸出援手。各類型新製節目陸續登場,取代不知播了多少回的盤帶音樂。廣播前輩陶曉清的經驗傳授;蔡琴、周治平、梁祖崇義氣相挺;殷正洋、蔡依林、薛志正的友情贊助;還有一群默默協助的義工朋友,無不讓我感念在心。 那段日子,當華燈初上之際正是電台開始活絡之時,義工們會陸續從工作崗位下班趕赴電台預錄節目。我總愛在錄音室外默默地聆賞著世界上最優美的樂音,最後再誠摯地獻上感謝的眼神。當時,父親常玩笑式地問我:「一個快倒的電台,你怎麼還可以忙到九、十點下班?」我總是微笑以對,但心裡卻堅定地告訴自己「她將風雲再起!」。 在歡慶台北電台走過「精采五十年」,正邁向下一個「輝煌五十年」之際,曾經是台北電台一份子的我,最想說的一句話是:「感謝有您,敬愛的義工朋友」。
「有太多的驚奇,就在你隔壁,台北廣播電台」。這段由蔡依林、殷正洋義務錄製的jingle,十餘年來不時迴旋在腦海,只為提醒自己「永遠不能遺忘那群在電台最潦倒時期,曾經伸出援手的節目義工。」 1996年8月1日凌晨台北市議會在李姓女議員主導下,以「黨政軍應退出媒體」為由,如數刪除台北電台八千餘萬元的人事及業務預算。台北電台瞬間由盛轉衰幾近歸零,百餘位員工面臨移撥或失業命運。我雖未經歷團隊崩離的感傷和不知誰掌管明天的茫然;但兩年後我卻接掌了百廢待舉、形同廢墟的「萬貫家業」。 在沒人、沒錢的窘境下,電台為保留執照,依舊維持十八小時播音(貼切說法是墊音樂)。不忍讓曾經叱吒風光的電台在我手中斷氣,不願扮演末代台長的我,開始捲起袖子向外求援。在師長、同學、朋友的穿針引線下,與我素昧平生的廣播界、藝文界、影視界、電台老同事及素人義工近三十人,竟然如即時雨般地適時伸出援手。各類型新製節目陸續登場,取代不知播了多少回的盤帶音樂。廣播前輩陶曉清的經驗傳授;蔡琴、周治平、梁祖崇義氣相挺;殷正洋、蔡依林、薛志正的友情贊助;還有一群默默協助的義工朋友,無不讓我感念在心。 那段日子,當華燈初上之際正是電台開始活絡之時,義工們會陸續從工作崗位下班趕赴電台預錄節目。我總愛在錄音室外默默地聆賞著世界上最優美的樂音,最後再誠摯地獻上感謝的眼神。當時,父親常玩笑式地問我:「一個快倒的電台,你怎麼還可以忙到九、十點下班?」我總是微笑以對,但心裡卻堅定地告訴自己「她將風雲再起!」。 在歡慶台北電台走過「精采五十年」,正邁向下一個「輝煌五十年」之際,曾經是台北電台一份子的我,最想說的一句話是:「感謝有您,敬愛的義工朋友」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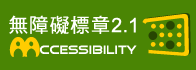
![我的E政府 [另開新視窗]](/images/egov.png)
